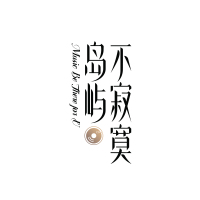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2月5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四国的海空军部队在菲所谓“专属经济区”举行第六次多边海上合作活动(MMCA)。日本媒体指出,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四国首次举行联合行动。
而就在两周前的1月21日,美国新任国务卿鲁比奥在华盛顿主持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新一轮的“四方安全对话”(以下简称“四国机制”),这也是本届特朗普政府的首场重要外交活动。

2025年1月21日,美国新任国务卿鲁比奥在华盛顿主持了美、日、澳、印新一轮“四方安全对话”。
尽管特朗普就职当日就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随后宣布对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及中国等加征关税,这一系列操作与其一贯宣称的单边主义一脉相承,但种种迹象表明,进入2.0时代的特朗普政府对“小多边主义”却似乎另有安排。
美国“小多边主义”战略的蜕变
“小多边主义”并非美国战略界的首创,早先被大量用于经济领域。不少双边或者区域自贸协定提出了包括原产地原则、知识产权保护等条款,这些安排或多或少都有明显的排他性和针对性,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互斥性。但是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占据主要位置,国家间的合作并不会因为区域经济合作而受到限制甚至出现对抗性。
但是当把“小多边主义”移植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对抗性、竞争性、针对性、排他性的特点就更为凸显。政治安全领域的“小多边主义”理念在美国战略界自冷战结束初期就已有产生,但并未成为主流。在“全球政治重回大国竞争时代”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在第一任期正式将这一理念置于与双边同盟体系同等重要的位置。
根据提前解密的印太战略框架,特朗普1.0的重要目标是协调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创建以美国为原则性中心的“四国安全框架”。同时,当时特朗普政府还提出强化美、日、澳三边合作的计划。2017年特朗普政府正式恢复“四国安全机制”,并逐步从司局级升格为外交部长级。
但是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小多边主义战略的实施。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科技战使得日本、澳大利亚、及东南亚国家等合作伙伴一时间难以适应,美国在南海针对中国频密、高强度、高风险的空中抵近侦察、情报搜集和威慑行动,也让这些国家对于可能卷入美中冷战甚至热战提心吊胆。这两方面因素使得地区国家与中国保持一定距离,美国的“小多边主义”战略也因此得不到盟友和伙伴最大程度的配合。
拜登政府上台后,在“重回盟友和伙伴”和塑造中国周边环境的战略框架下,美国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对华竞争策略,包括重新寻求与中国就军事安全危机管控保持对话,经济上也推出了旨在安抚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印太经济框架”。加之,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也渐渐适应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科技战所带来的影响。得益于此,拜登政府在“四国机制”和美日澳基础上,构建了美日韩、美日菲、美英澳、“四国+”等一系列政治安全合作机制,将“小多边主义”战略推向了新的高度。

2024年4月7日,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在南海举行联合海上演习。
特朗普2.0时代“四国机制”面临挑战
自2017年重启,“四国机制”渐渐成为美国试图重构印太地区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齿轮,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不仅配合和融入美国巩固区域霸权安排,更是为美国强化经济和军事霸权提供了帮助。
比如,2022年9月“四国机制”东京峰会提出的“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计划”实质上就是美国旨在建立情报霸权的印太海域态势感知计划的一个部分,日本、澳大利亚的加入不仅使美国完善印太海上情报网络布局成为可能,更是通过雷达、巡逻船等装备及训练等方面的援助,帮助美国将覆盖海、陆、空、天的海上情报系统扩大到南太平洋岛国、东南亚及本地区其他国家。再比如,“四国机制”在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推进中同样发挥着“马车”的作用,是拜登政府联合本地区国家竞争区域经济秩序主导权的“供应链联盟”等的主要支撑。
经过两届政府的积累,“四国机制”确实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运作机制,同时也设立了一系列的区域合作项目和计划。拜登政府期间,四国机制举行了6次领导人峰会、8次外交部长会议,这些进展为特朗普时代的四国对话与合作奠定了基础,尤其是设定了议题讨论框架和推进轨道。然而,这些成果多数都是拜登留下的遗产。
从历史的经验看,单边主义和美国主义占据主流思潮的特朗普政府显然无法和奉行“小多边主义”理念的拜登政府相提并论。特朗普2.0时代,“四国机制”至少面临三个方面挑战。
第一,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将打乱甚至部分阻断“四国机制”的现有格局安排,考验其他成员国对美国的耐心。
自2021年9月的首次领导人峰会,“四国机制”已经初步建立议题框架,包括气候变化、清洁能源、海洋安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这些议题既是当前全球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前沿,但更是四国基于求同存异的原则所梳理出来的共同议题,一方面体现了四国的共同利益或兴趣,另一方面也隐藏了不为人知的利益交换和相互妥协。
然而,特朗普上台后,仍然将单边主义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这必然会对现有基于多方协调和体现各方利益的议题造成冲击。比如,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必然使得四国围绕全球健康和健康安全、公共卫生安全、气候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遭受挫折,在压缩四国合作潜力空间的同时,也将削弱印度等其他成员国对美国的耐心。

2024年12月2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日本外相岩屋毅(左)与中国外长王毅在双边会议前握手。
第二,“美国优先”考验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信心。
1月20日,特朗普政府发布上任后的第一号新闻稿,系统描述了“美国优先”政策的优先项,这清楚说明其仍将延续一贯政策。“美国优先”的原则强调避免将资源和注意力浪费在新的外围冲突上、惩罚“搭便车”的盟友、专注于与中国的竞争等各个方面。因此,上任后数小时内,特朗普下令暂停对外援助90天,此后又敦促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改变在世界各地分配援助的方式,以符合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特朗普要求北约国家将国防预算增加至GDP的5%,此举引起了日本国内社会的担忧。
美国试图通过“四国机制”,提升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彼此间的协调与合作,合力扩大面向本地区的安全和经济公共产品。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出于各自利益诉求,配合并参与这一机制。但是“美国优先”无疑将增加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对地区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贡献比例,而自身并非一定获得同等比例的收益,这三国将反思参与“四国机制”的现实意义,对与美国合作能带来的收益及美国愿意为了共同约定的利益可以投入的资源产生怀疑。
第三,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将再次对日本、澳大利亚及印度投入大国竞争的决心发出拷问。
在“四国机制”建立之前,印度对于美国发出的参与南海海军联合巡航的提议明确拒绝。时至今日,印度依然未能加入美国发起的南海联合巡逻。印度直到2020年才同意澳大利亚加入“马拉巴尔”联合军事演习。印度的这一系列“犹豫”被广泛认为是“四国机制”的“薄弱环节”,但同时也反映出其对美国试图将这一机制打造成为“反华安全集团”持有不同意见。即使中印之间围绕边境争端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件,印度战略界的主流观点仍然担心,一旦“四国机制”过度激怒中国,将可能引起中国在印度洋和巴基斯坦问题上对印度的“报复”,因此印度侧重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保持非传统领域的合作,在战略和传统安全问题上保持平衡。
另一方面,日本石破茂政府近日表示“日本首相访问中国是极为重要的事”,这有助于两国探索彼此的利益,“绝对不能让中国诉诸冒险主义的武力手段”。日本政府去年底以来的表现,被视为是试图在美中之间建立某种平衡。日本并未改变联美制华的战略,但石破茂政府试图避免日中对抗升级的用意明显。
澳大利亚同样对可能因为中美竞争升级而波及中澳关系表现出担忧,澳总理阿尔巴尼斯1月初表示“相信自由贸易,而不是保护主义”,不会因为中美竞争而改变对华政策。
特朗普1.0重启“四国安全机制”的出发点是侧重安全领域、打造一个赢得对华竞争优势的“集团”,拜登政府意识到了过度侧重安全领域将引起其他成员国的抵触,因而转向非传统领域。特朗普政府再度上任之后,公开提及“美国主义”和“昭昭天命”,这意味着其依然将大国竞争定义为当下国际体系的主要特点。特朗普的智囊团班子亦有不少持中美关系陷入“新冷战”的观点。特朗普政府以“新冷战”和大国竞争作为前提假设的印太战略与政策设计,将再度检验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决心及“四国机制”的团结性。
基于“四国机制”的小多边合作将虚大于实
诚如所言,“四国机制”已经成为成熟的小多边机制,司局级、外交部长和领导人之间的磋商仍将持续。如果说2021年2月的四国外长会议是为了将四国安全对话升格为领导人级别,那么鲁比奥和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三国外长的华盛顿磋商,就是为了确认美国所做出的承诺依然有效,将延续“四国机制”的已有安排。但鉴于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美国优先和美国主义等指导理念的冲击,笔者认为,四国的务实合作难言可期,彼此磋商将以务虚议题为主。

2020年11月17日,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的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印度洋进行“马拉巴尔”联合军演。
第一,海洋安全将依然是四国对话与合作的主要议题。海洋是支持美国印太地区霸权的核心空间,是澳大利亚、日本对外贸易与国家安全的主要地理环境,也是印度战略与安全的主要区域,因此必然是四国展开安全对话与合作的天然共同话题。印度虽然无意在南海有关争议上过度激怒中国,但其在印太部署、公开肯定南海仲裁案裁决等已经采取的措施和立场,并不会改变。日本和澳大利亚对菲律宾及其他声索国以南海问题为主要议题的双边对话与合作,亦不会受到削弱,因为两国视南海问题独立于对华关系,且无意忽视东南亚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及与东盟国家关系的重要性。
鉴于此,“四国机制”对于海洋安全领域的已有安排还将持续,包括推进“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计划”等。南海和东海问题也依然是四国对话绕不开的话题,但印度不会改变维持平衡和两边观望的政策。
第二,“四国机制”将进入“瘦身”时代。“四方安全对话”虽被冠以“安全”,但事实上自拜登政府,四国所讨论的话题覆盖了印太地区的公共卫生、数字经济、海洋、反恐、人道主义救助等非传统和传统安全领域。然而,受特朗普政府政策倾向的影响,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对外人道主义等议题的合作未来将因为美国缺乏合作意愿,而不得不面对转向甚至暂时搁置的局面。
因此,可以预见,“四国机制”目前所覆盖的领域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会大幅度缩减:一方面,公共卫生、全球健康、气候变化等部分议题被暂时叫停几乎没有悬念;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对外援助政策的调整意味着四国围绕印太地区人道主义援助的合作也会随之进行调整。总之,特朗普2.0时代,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彼此间的共同话题因为“美国优先”“美国主义”的复苏而面临“裁员”的困局。
第三,四国合作将从“务实”向“务虚”转变。拜登政府之所以将“四国机制”逐步转向聚焦非传统安全领域,其主要原因在于四国围绕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存在较大分歧。基于此以及拜登政府寻求务实合作的决心,四国在海域态势感知、海底电缆、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倾向损害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侧重大国竞争的战略取向将使得四国的对话议题逐渐向传统安全领域集中。显然,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在针对包括中美竞争、大国合作等传统战略性问题上,彼此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相互间的对话将只是一种对话,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保持对话节奏是这一机制得以保持的主要原因,寻求实际合作将成为次要的任务。
总之,特朗普2.0时代,美国对外政策指导原则的变化将改变以“四国机制”为代表的美国“小多边主义”战略的进程。特别是在针对中国方面,美国虽然执意利用这一机制遏制中国、重塑印太地缘政治结构,但对于卷入中美竞争,各国存在不同的考量,这一方面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美国主义”与美国冷战结束后的一贯战略和价值取向格格不入,令人难以适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与中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斩断与中国的利益纽带。
(作者:陈相秒,中国南海研究院南海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华阳海洋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