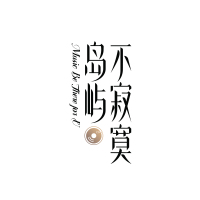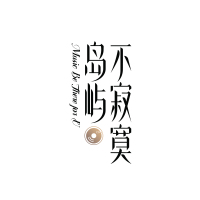











亚太安全格局正经历结构性调整。近期日本与菲律宾频繁的军事互动有几个关键节点:
其一,日本防务大臣中谷元今年3月访菲期间提供的FCS-3A相控阵雷达系统,使菲律宾对南海监控半径从120海里跃升至350海里,再配合“美日菲+X”情报网络,实现了对20万平方公里争议海域的立体化监控;
其二,5月《互惠准入协定》生效后,日本自卫队首次获得菲律宾境内军事训练权,随即6月“高波”号驱逐舰与菲方“米格尔·马尔瓦尔”号护卫舰就在吕宋岛北部海域开展联合演习,标志着日菲装备协同进入实操阶段,完成日菲“安全伙伴”向“准同盟”的质变;
其三,几天前的7月6日,日本表示已就首次对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与菲达成协议,进一步提升日菲军方的协同作战能力。
这种“能力建设”包装下的“军事联姻”蕴含三重安全悖论:
首先,战略误判引发安全反噬,日本借“支援”突破和平宪法第9条,菲律宾以“主权典当”换取装备,二者均陷入偏执的“安全幻觉”;
其次,技术扩散导致区域军备竞赛螺旋升级,雷达系统与巡逻机的部署使南海军事化进程加速;
再者,主权让渡侵蚀国家自主性,为与中国对抗菲律宾将大部分国土纳入他国监控体系范围,实质形成“主权抵押”的新型依附关系。
历史经验表明,军事同盟存在着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当前日菲合作已突破传统“能力建设”范畴,形成“装备转移-情报共享-联合行动”的完整军事链条。这种“军事联姻”犹如双刃剑:短期虽提升菲在区域内的存在感,但长期将导致安全复合体固化,使亚太地区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预置风险。
当二手舰艇成为战略支点,当相控阵雷达化作监控枷锁,地区国家终将为这种非对称安全合作支付既削弱主权完整性,又加剧战略不确定性的双重代价。
战略误判:依附性合作陷阱
日菲强化军事合作本质上源于对美战略承诺的路径依赖与历史经验认知缺失,其对抗性思维定式折射出零和博弈逻辑的深层困境。
这种战略互信机制的脆弱性体现在以下两个维度:一方面,地缘政治博弈中过度依赖单极权力保障,忽视多边安全架构构建(如东盟中心性原则);另一方面,安全合作模式呈现“安全困境”的典型特征——军备竞赛指数增长与危机管控机制严重滞后并存。
这种基于结果导向而非过程治理的战略选择,是缺乏内生增长动力的外生依赖型模式,其结构性缺陷在南海局势复杂化背景下将加速显现,最终导致战略收益边际递减而风险持续扩大。
从战略博弈视角审视,美国承诺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
首先,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已形成路径依赖,其“选择性盟友”策略在乌克兰危机中显露无遗——北约东翼国家被迫承担巨大军事补给压力,而美国却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将战略资源向本土产业倾斜。
这种“战略透支”模式在印太地区同样显现,据公开数据显示,美军南海常态化军事存在已逼近极限,军装备老化与力量投射能力出现疲态。而拜登政府承诺的40亿美元“印太经济框架”专项基金,也因其任期结束而不了了之。
这种承诺失效的深层逻辑在于美国地缘政治能力的系统性衰退。
当日本将一半以上的国防预算增量押注于“延伸威慑”,菲律宾耗巨资在南海争议海域部署武器装备及舰艇时,这种“战略负债”模式导致日菲两国陷入“安全依赖陷阱”,其国防预算中域外力量依赖度远超正常国家的战略安全阈值。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承诺体系正在经历结构性解构。
从“四方安全对话”的预算缩水,到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的条款虚化,这种“承诺通货膨胀”本质上是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回撤的必然结果。
米尔斯海默说:“当霸权国无法兑现承诺时,最明智的选择是及时止损而非强行维持。”这种地缘政治博弈的深层逻辑,正在重塑亚太安全秩序的底层架构。
秩序颠覆:东盟分裂与军备竞赛的“多米诺效应”
日菲近期签署的《互惠准入协定》与《海上联合训练协议》,表面冠以“构建区域安全秩序”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之名,实则通过军事部署常态化与情报共享机制,系统性削弱东盟主导的“东盟+”安全架构。
这种战略选择不仅动摇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确立的对话协商的根基,更可能引发“安全困境螺旋”——根据公开报告显示,2016-2024年间域外国家军事演习频次大幅增长,直接导致区域信任赤字扩大至历史峰值。
这种以“阵营化”对抗“共同体”的路径选择,迫使地区国家陷入“安全承诺不可信”的困境。
区域合作机制的结构性裂变也呈现多维表征。菲律宾与日本签署军事基地共享协议,这种安全领域的深度绑定直接动摇了东盟组织架构的稳定性。越南在强化与韩国军事装备合作的同时,拒绝参与美日菲三边联合军事演习,形成安全政策层面的“选择性疏离”。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共同体裂变呈现更显著的制度性特征。
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率先构建区域本币结算机制,将菲律宾排除在外,这种制度性排斥导致东盟内部形成“经济防火墙”。根据东盟秘书处年度贸易监测报告,区域内贸易依存度已从2019年的28.7%降至2023年的24.3%,印证了区域经济整合的实质性弱化。
这种分化态势本质上是成员国基于风险收益评估的理性选择,但在安全领域却呈现“安全同盟嵌套”特征,即菲律宾与美日构建“印太战略支点”,越南则通过“非对称装备采购”维持战略平衡。
更深层次的影响体现在制度供给层面,当既有框架无法满足成员国的差异化诉求时,“制度性替代方案”的涌现便成为必然。
马来西亚战略学者翁忠义指出,东盟的存续机制不依赖共识达成,而在于构建包容多元立场的制度框架,这种“制度容器”理论在当前危机中正面临严峻考验。
区域安全架构异化引发连锁性军备竞赛并催生虚幻安全认知。日菲安全协作机制的确立,不仅加速了区域安全架构的异化进程,更通过战略威慑的传导效应,引发东南亚国家安全决策的系统性偏移。
这种“威慑—反制”的螺旋机制,使南海安全态势呈现出典型的“安全困境”特征,逐渐导向形成非对称军备竞赛格局。这种“威慑—反制”的螺旋机制,不仅导致安全成本几何级增长,更使区域战略互信持续弱化。
“主权典当”:技术依赖与国家空心化
菲日军事合作框架下的制度性主权让渡,正使菲律宾对日本形成新型依附关系,这种非对称性合作模式,对东南亚国家的战略自主性构成持续性侵蚀。
从地缘政治经济学视角观察,日本试图通过“技术-资本-规则”三位一体的捆绑式合作,在军事基地准入、数字货币结算、半导体产业链重构等关键领域实施制度性约束,使得菲律宾的国防预算审批、关键矿产出口配额、跨境数据流动等核心决策权出现结构性转移。
这种隐性主权让渡的破坏性在于其渐进性和复合性。当技术标准、金融规则、数据主权相继被纳入外部体系主导时,国家战略自主性将面临比传统军事威慑更复杂的系统性风险。
技术援助中的隐性控制机制。日本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OSA)对菲军事援助,构建起典型的技术捆绑体系。该机制通过三个维度实施战略控制:
其一,强制推行日制数据链标准,提供给菲的FCS-3A雷达原始数据直连东京防卫省情报本部,形成“数据采集-分析处理-选择性反馈”的闭环系统;
其二,日本重工实施对菲海军装备实施核心技术封锁,具体表现为动力系统图纸解密等级限制和关键部件采购绑定条款等;
其三,构建“技术依赖-战略依附”的共生关系,菲海军本土维修能力远不能覆盖设备寿命周期。这种技术依附关系已使菲律宾在南海争议中陷入“战略被动”,其军事行动自由度逐渐受制于人。
根据《互惠准入协定》条款,日本自卫队被赋予近似美军基地的准入权限,实质构成对菲律宾司法主权的隐性侵蚀。这种操作复刻了冷战时期美国海外驻军的扩张模式,其制度设计本质上延续了单极霸权体系下的军事同盟范式。
国际法学者指出,此类非对称安全合作机制通过技术性条款突破主权边界,使东道国陷入“主权让渡-安全依赖”的恶性循环,这种现象被认为是新型国家空心化的表征。
地缘经济博弈也呈现出技术殖民的新形态。
菲律宾政府以程序瑕疵为由暂缓中菲苏比克-克拉克铁路项目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随即推出年利率仅0.1%的特别融资方案。该方案表面遵循国际开发援助惯例,实则捆绑了严苛的条件,例如项目必须采用日本标准、聘用日籍监理、采购东芝三菱设备等。
这种“技术标准捆绑”模式,使受援国基础设施体系深度嵌入日本产业生态链。菲律宾制造业因此丧失技术升级自主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被锁定在产业链中低端,彻底背离国家工业化战略目标。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日菲缔结“准军事同盟”,以冷战对抗思维构筑遏华“小圈子”与中国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地区国家对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愿景格格不入。
日菲“军事联姻”的实质是地缘博弈与战略误判的叠加。日菲防务合作非但不能缔造安全,反而成为亚太和平的最大变量。其本质是美日地缘野心与菲律宾政治短视嫁接的畸形产物——日本借此突破“和平宪法”禁锢,美国完成印太拼图最后一环,而菲律宾则幻想以主权典当换取廉价保护伞。
当日本自卫队战机从巴丹半岛起飞时,菲律宾人是否想起1942年同一片天空下的零式战机?当马尼拉为350海里雷达覆盖范围欢呼时,可曾计算国民为国防预算付出的教育医疗等民生代价?
真正的安全从不由他国军舰定义,国家安全的核心价值根植于主权完整与民生保障的辩证统一。这种认知范式突破传统地缘政治的二元对立,为地区国家构建新型安全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点。维护战略自主权与提升民众获得感,构成国家安全的双重支柱,二者共同构成抵御外部干预的韧性屏障。
(作者:胡鑫,中国南海研究院北京分院执行主任、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