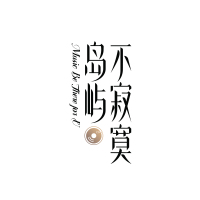伴随美国对华战略调整,日本依托日美同盟也在不断调整其亚太政策,其南海政策也在深度嵌入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战略性的调整。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鞠海龙及博士研究生卢美帆日前在《日本学刊》发表《从战术性渗透到战略性应对:日本南海政策分析》一文,认为日本南海政策是日本长期依托日美同盟推进自身亚太政策过程中形成的区域性地缘政策。该政策并非以独立政策文本的形式展现,而是散见于日本对华、对东盟国家和相关地区事务的政策碎片中,带有较强隐蔽性。伴随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其分散在各领域的政策经由南海地区事务关联中国周边安全的逻辑线索,也日渐清晰。
如今来看,日本的南海政策已从碎片化的“战术试探”升级为系统性的“战略应对”,而这一转变并非偶然,在本质上是日本延续性奉行地缘对抗战略的必然结果。当然,这也是外部战略环境和日本的国家目标、国内政治共振的结果,其影响正穿透南海海域,辐射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
从政策轨迹看,日本的渗透早有铺垫。
20世纪70年代,日本通过“福田主义”和 “赔偿外交”消解东南亚战争记忆,在文化和情感上增强了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随后不断通过经济合作的渠道,逐步将文化、情感与经济影响转化为政治影响。
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在地区的经济影响力逐步“外溢”,延伸至安全领域,通过1999 年《周边事态法》将南海纳入“周边”,借助2015 年“新安保法”突破海外用兵限制,为介入南海扫清法律障碍。不过,此时的政策仍属 “隐蔽推进”,核心是依托日美同盟“借势布局”。
2022年无疑是日本南海政策的转折点。

2024年4月7日,美国海军“移动”号濒海战斗舰参加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在南海举行的联合军演。
“新安保三文件”明确将中国定为“最大战略挑战”,军费预算连年攀升,在2024年达 7.95万亿日元。同时,日本在南海地区的行动更具攻击性,不仅与菲、越等国建立“2+2”安全磋商机制,向菲律宾交付可监测黄岩岛的雷达设备,还推动形成日美菲、日美澳菲等小多边机制。2024 年,日本联合美澳菲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甚至计划 2025年开展海岸警卫队联合巡逻。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正成为北约“亚太化”的“跳板”,2024年北约外长会议邀请日本参与,英、法航母相继赴南海“巡航”,背后均有日本的推动。
日本南海政策的战略转型有其国内外多重影响因素和逻辑。

2024年7月28日,美国国务卿、美国国防部长、日本外交部长、日本防卫大臣木原稔出席日美“2+2”安全会谈。
具体来看,这包括:其一,日美同盟的“战略绑定”:美国将南海作为对华遏制支点,日本则借同盟突破“专守防卫”,2024年日美 “2+2”会谈明确“战时统合指挥”,实质是日本将自身安全诉求嵌入美国“印太”架构。其二,“政治大国”的目标驱动:中国经济总量 3.6倍于日本的现实,让日本对地区影响力流失感到焦虑,试图以南海为抓手重构对华制衡格局。其三,国内政治发展的助推:日本国内“修宪”势力掌控议会,民众对“扩军”支持率更是从 2000 年的 13% 升至 2023 年的 41.5%。
日本南海政策的战略转向,本质上是其继续奉行地缘对抗思维的展现,势必将给地区带来显而易见的风险。一方面,日本打破了南海合作“经济优先”的传统,将东南亚国家拖入 “安全对抗”,特别是菲律宾接收日本军援后,与中国的海上摩擦频次增加,印证了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被工具化”的担忧。另一方面,日美同盟与北约的联动,可能让南海成为 “规则对抗”的试验场,日本鼓吹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实质是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地区国家主权之上。
当然,从长远看,日本在南海的战略转向难以为继,存在多个难以把控的结构性矛盾。一是,日本经济命脉依赖南海航线与推动航线成为“冲突热点”自相矛盾,二是推动修宪成为“正常国家”的战略自主努力与依托日美同盟、交心北约相矛盾。

2025年2月24日,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特·特奥多罗与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菲律宾马尼拉进行会谈。
对中国和东南亚等地区国家而言,日本南海政策的战略转向是需要警惕的。中国需警惕其“小多边包围”策略,同时与东南亚国家开展 “经济合作 + 安全对话”,避免南海局势升温。对东南亚国家而言,日本的“安全诱饵”虽然给了更多的选择,但在本质上与美国“印太战略”对地区的安全风险绑架无异。
由此,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唯有保持战略自主和南海对话渠道的顺畅,以及在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基础上推动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才能推动南海区域治理规范,促进南海地区安全稳定与共同繁荣发展。
(作者:葛红亮,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副院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研究专家委员会”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