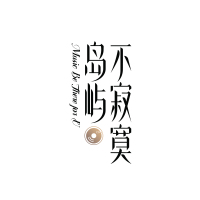“美国主张的航行自由,即‘我想怎么走我就怎么走,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8月25日,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美式“航行自由”法律评估报告》中英文版(下称《报告》)。《报告》撰写小组成员、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海文在发布会现场形象地指出美式“航行自由”的本质。

美式“航行自由”严重损害国际法则(漫画: 晨凌)
《报告》认为,美式“航行自由”包含大量美国自创概念、自设标准的所谓习惯国际法,与国际法和许多国家的实践相悖。美国借助这些主张和行动,极尽所能压缩其他国家的合法权益,扩大其权利和自由,以获取不受法律约束的“自由”。
美式“航行自由”的扭曲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公约》)及一般国际法中从来没有不受限制的航行权利。在《公约》中,既保障船旗国的航行合法权益,也尊重和顾及沿海国的主权与安全。《公约》这种平衡的设计其实是国际社会经历多年磋商达成的一揽子协议,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美式“航行自由”却打破了安全跟自由之间的平衡。
《报告》撰写小组成员、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郑志华在发布会上表示,美式“航行自由”不仅在海域范围上超越了《公约》的规定,不当地将这个概念应用到其他海域,还在具体内容上突破了《公约》对航行自由的合理限制,将航行自由视为一种绝对的权利。尤其是美式“航行自由”对《公约》的选择性适用,冲击了《公约》作为一揽子协议的性质;利用了航行自由概念存在的模糊地带,搞灰色地带胁迫;造成了国际社会对《公约》理解的歧义,这对于国际法治带来了很坏的影响。

《报告》显示,美式“航行自由”对航行利益的过度扩张,和对沿海国海洋权益的非法限制(摄影:沈湜)
为了拥有“美国利益至上”的绝对特权,美国创造了“国际水域”这一非法律概念。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海文指出,《公约》1982年通过之后,就没有“国际水域”这一概念,同时规定了每个海域适用不同的航行制度。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在世界上9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800多个军事基地,如果承认各国专属经济区归沿海国管辖,美国则无法保证其军事力量投送的自由。为了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开展军事活动找借口,美国强行将专属经济区与公海混为一谈,这种做法根本就是偷换概念,并创造新的概念,以避开《公约》现有、明确的规定。
选择性实践下的美式“航行自由”
1979年,美国为反对拟议中的《公约》拓展沿海国管辖海域的部分,出台了包括外交和军事行动在内的“航行自由行动”,这个行动持续至今。
打着“航行自由”旗号,美国标榜其“航行自由行动”不针对特定国家。华阳海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包毅楠在接受南海之声采访时表示,近 30 年的实践数据揭穿了这一谎言。从美国公布的数据来看,被“航行自由行动”挑战的国家中,亚洲国家占比始终保持在60%-70%,东南亚是“重灾区”,中国则连续多年成为被挑战事项次数最多的国家。“这种明显的区域倾斜绝非偶然,这与美国‘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深度绑定,本质是通过航行自由行动,遏制中国等亚洲新兴国家的海洋影响力。”

航行不是“横行” 自由不能违法(漫画: 晨凌)
包毅楠认为,即便美国偶有挑战日本、菲律宾等盟友,也多为 “象征性操作”。对中国、伊朗等“战略对手”,其挑战则更具针对性:在南海,聚焦中国岛礁主权与领海基线划定;在霍尔木兹海峡,紧盯伊朗对国际能源通道的管控。这种选择性实践暴露了美式“航行自由”的真实目的,通过控制关键海域、打压战略对手,服务其全球霸权布局。
航行自由从来就不是霸权的工具,国际海洋秩序也不应由单一国家主导。包毅楠表示,美国若真有意维护航行自由,最基本的一步便是批准和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只有成为缔约国,“坐在同一桌上”,才能谈得上用同一套规则办事,而非以“局外人”身份对缔约国指手画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