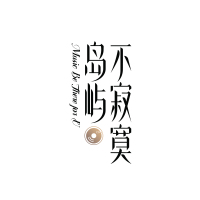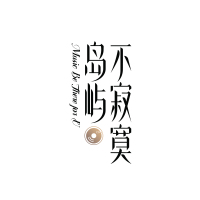











“当我们的岛屿被塑料垃圾无情淹没时,发达国家却在吝啬地讨论‘捐赠多少’,这绝非真正的合作,而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
8月15日,为期11天的新一轮全球塑料污染治理谈判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落下帷幕。会上,来自太平洋岛国图瓦卢的谈判代表在会上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无奈。
这场本被寄予 “收官” 厚望的全球性磋商,却未能形成可提交外交大会审议的条约文本,这再次印证了塑料污染全球治理的艰难性。
此次会议中,来自183个成员国、400多个观察员组织的2600余名代表围绕涵盖塑料全周期管理的协议草案展开审议,期望推动从设计、生产到处置的系统性变革,进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大幅减少塑料流入环境。但现实是,各国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在关键议题上僵持不下。
以初级塑料聚合物管控为例,欧盟与部分环保意识较强的国家组成“高雄心联盟”,主张将全球塑料年产量上限设定为3亿吨(当前为5亿吨),并要求在2040年前实现一次性塑料减产40%,从源头上遏制塑料污染。但美国、沙特阿拉伯等“低雄心联盟”国家坚持“自愿减排”,认为强制管控将损害本国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
资金机制的讨论同样陷入僵局。发展中国家联盟呼吁建立“塑料污染治理专项基金”,期望发达国家每年出资至少100亿美元,助力其建设塑料回收设施、推动技术升级。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表示仅接受自愿捐赠,承诺金额累计不超过30亿美元。更关键的是,资金来源、分配与监督的法律语言仍停留在“模糊表述”,缺乏清晰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排。太平洋岛国图瓦卢的谈判代表在会上指出:“当我们的岛屿被塑料垃圾无情淹没时,发达国家却在吝啬地讨论‘捐赠多少’,这绝非真正的合作,而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 南北国家在资金问题上的尖锐对立,严重影响了谈判的整体进程。
而在规则适用范围上,各方分歧同样显著。“高雄心联盟”主张将微塑料、塑料添加剂等全面纳入管控范围,以实现全方位治理。但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忧心此举会变相限制本国工业的发展,坚持仅对一次性塑料制品进行管控。在会议的最后阶段,尽管各方试图通过模糊表述来暂时弥合分歧,但最终发布的草案中,关于管控范围的描述依旧充斥着 “酌情考虑”“视情况而定” 等模糊词汇,这无疑反映出各方在该问题上难以达成明确共识,也让未来的塑料污染治理工作充满不确定性。正如绿色和平组织塑料污染项目负责人所感慨的:“这次谈判再次无情地证明,在塑料污染治理问题上,各国仍在‘以共识之名,行拖延之实’”。
此外,谈判中还存在其他核心争议焦点。在污染责任划分上,围绕“现存”还是“历史遗留”塑料污染的措辞存在分歧,这关系到责任承担和资金分配机制。不少发展中国家主张“历史遗留”,发达国家坚持“现存”。最终案文采用折中方案,使用“现存及历史遗留塑料污染”。在公正转型与健康问题上,“高雄心联盟”要求公约包含公正转型责任和塑料对健康影响的内容,“低雄心联盟”认为相关科学证据不足,建议先加强研究。最终案文保留条款,要求各主体在自身条件和能力下促进公正转型,加强相关科学技术研究与合作。
此次日内瓦谈判的僵局,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全球塑料污染治理体系深层矛盾的集中爆发,主要体现在跨境流动、利益纠葛与制度碎片化这三个相互交织的维度。
塑料污染的跨境流动,导致污染责任难以界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5年报告显示,全球每年有1300万吨塑料垃圾通过合法或非法渠道实现跨国转移,其中80%流向环境监管相对宽松的发展中国家。2024年,越南海关查获的1.2万吨非法进口塑料垃圾,大多源自欧洲,却在越南的河流和农田中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永久污染。
更为棘手的是自然力驱动的跨境污染:“太平洋垃圾带”每年向周边岛国输送约40吨塑料,原产地涉及全球100多个国家,责任认定犹如大海捞针。德国莱布尼茨研究所的研究证实,通过大气环流传播的微塑料已实现“无国界分布”,北极冰芯中30%的微塑料可追溯至亚洲的塑料生产基地。这种“生产在甲地、消费在乙地、污染在丙地”的复杂链条,打破了传统的“属地管辖”原则,导致全球治理陷入“谁都该管,谁都不管”的尴尬困境。
经济利益的深度纠葛,阻碍治理行动推进。全球塑料产业链呈现“上游垄断、下游承压”的畸形结构:主要塑料生产国牢牢控制着大部分的初级塑料产能,却将90%的废弃物处理压力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导致各国在治理立场上出现显著分化。
欧洲凭借年产值420亿欧元的生物基材料产业,积极推动《一次性塑料禁令》以实现绿色转型。而塑料制造业占GDP比重高的东南亚国家,因经济发展对塑料产业依赖度较高,坚决反对激进管控,担心这会对本国经济增长和就业造成严重冲击。
制度体系的碎片化,使得治理行动难以形成合力。目前全球有140多个国家的单边塑料管控政策及23个区域性协议,但这些规则在管控范围、执行标准、处罚力度上差异巨大。
以南海沿岸国的治理实践为例,中国海南省2020年就通过立法构建全链条治理体系,制定禁塑名录负面清单并建成可追溯管理平台,同时运用“海上环卫”系统和监测浮标实现海洋防控。越南虽已敲定禁塑时间表(包括2026年禁售小尺寸不可降解塑料袋)并引入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但政策落地面临替代品成本高、回收体系碎片化等现实挑战,目前全国塑料回收率仅为27%。菲律宾则因部分区域非法活动缺乏规范,每年约300吨固体垃圾被直接排入南海,对珊瑚礁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这种区域内的治理差异与全球层面的规则混乱形成呼应。
更严重的是,塑料污染治理尚未形成像气候变化领域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那样被广泛认可的原则——发达国家强调 “共同责任”,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同等管控义务,发展中国家则坚持 “历史贡献度”,主张根据塑料消费量和污染贡献度合理分配责任。这种原则性分歧导致全球治理始终停留在“口号共识”阶段,难以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实际行动,使得全球塑料污染治理工作在混乱与无序中徘徊。
面对谈判挫折,全球塑料污染治理的下一步走向备受关注。各方将目光投向 今年12月在内罗毕召开的第七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作为设立并调整INC授权与议程的“母会”,联合国环境大会并不直接通过“塑料公约”文本,但将决定INC-5.2僵局后的路径:是延长INC授权设定新的谈判时限,还是采取更小范围、多边/区域的协商模式?这并非“无限期拖延”的信号——各国将通过表决或协商确定未来机制,不排除对授权进行精细化和限时化的设定,甚至提出替代性路径或终止进程。
全球性环境危机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要各国能够摒弃狭隘的自身利益观念,从人类共同命运的高度出发,在分歧中积极寻找共识,在博弈中努力谋求共赢,终将找到破解困局的有效路径。也正如此次谈判的会议主席路易斯·瓦亚斯在会上所言:“历史并非建立在安逸之上,而是建立在勇气、团队合作和妥协之上”。
(作者:吴磊,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